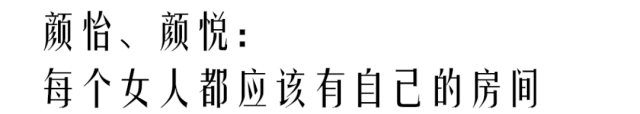我们也许素不相识,却从彼此身上获得了莫大的慰藉和帮助。 采访:朱凡Juvan Zhu 摄影:Irving Penn,美国版VOGUE 1985年9月刊 最近,我们依旧在保持创作。 写自己的戏剧、小说,也在写脱口秀,计划明晚就去开放麦讲一讲,新稿子的主题是关于职场的。大学一毕业我俩就直接进入职场了,对这个话题还有挺多体会的。 告别脱口秀大会5,如果说遗憾,一定是有的,最后一场没有达到一个好的结果。但其实也没有那么遗憾,因为今年的状态、整体创作,包括表演,都受到一些影响,又想去谈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感觉是挺难的。对于今年的表现,我们只能是尽力在标准线下挣扎。 我们自己就是女性,首先关注的就是自己的生活。脱口秀这个表演门类,讲述和表演者相关的话题,更容易打动人。女性这个主题也不是刻意找的,是后来慢慢发现,原来我们在脱口秀上讲的一些主题是在讨论女性相关的话题。最初就是在网上或线下,听到一些关于女生化妆、容貌焦虑等问题不太成熟的观点,我们觉得可以说得比他们好,能说得更透彻。 慢慢地,我们也会有意识地去研究女性主义,接触更多关于女性议题的内容,从这又学到了新的东西,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正向循环。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关注社会议题,从社交媒体去看这个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同时也很关注出版的女性著作,从她们身上薅取一些灵感。最近在看上野千鹤子的《始于极限》,她是日本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现在已经70多岁,一直在写作与研究。她的有些观点,可能连女性本身都意识不到,甚至可以说是离经叛道。她不仅讨论女性主义,在养老及其他很多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固有认知,这是特别有力量的一件事,她用她的方式告诉你,其实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得到回应与共鸣。很多女性给了我们这种回应,也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去讲这些话题。其实今年特别想要写一套段子,虽然会挺难的。就是想表达,为什么能够站在舞台上的有话语权的女性这么少,很多女孩会被当作粉丝,或者是另一个人的缪斯,而不是一个表达主体。 我们俩有彼此,已经占据了彼此的缪斯地位确实,有些事情男生不一定会有共鸣,但同时他们又是观众,我们也需要去获得他们的认同,不然在比赛中就很容易被淘汰。 女性互助中那种决心和勇气,是可以传递的。女性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一个女性遭遇一些事情时,现在会有其他的女性站出来,分享相似的遭遇,这种分享会让人觉得自己不那么孤独,没有那么恐惧。同时,也会逐渐建立一些信心,而不会总觉得是自己有问题。 脱口秀这个行业比较新,大家互相帮助的氛围很浓,平时也会在一起讨论。今年,整个录制过程有一种很强烈的漂泊感,但相互之间更加团结了,大家都在互相帮助,有一种再不互助就真的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的绝望。我们跟三弟一直互相帮助,虽然我们都挺惨的,也没有什么好成绩,鸟鸟也有来帮我们改稿子。 今年的录制是在青岛,影棚是在一个很大的园区,那里没有办法点外卖,所有东西都得自己带齐。有一天突然例假提前了,没有带卫生巾,只好到处借,最后好不容易借到了。后来,他们准备了,有其他女生用上了,还特意来找我们说感谢。有时候觉得,幸好我们是演员,有勇气去提出建议,能真正帮助到他人,我们真的很开心。或许是大家的生活突然出现了一种不可预测的改变,所以觉得不管想什么都应该立即行动,把理念付诸实践。 我们也会参与一些女性公益。比如“予她同行”的卫生巾捐助项目,及一些线下的活动,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想要参与支持。线下的交流也很有意义,女性互助,无非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只是在以前,会被拎出来特殊化。我们希望现在在做的事情,可以让更多的人在未来参与互助时不再大惊小怪,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爱。 告别比赛,回到上海,不仅是感到松弛,还有劫后余生的感觉,觉得既然没法讲出想讲的,还不如先不讲,看看未来会怎么样。这次录制又是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最难受的是,一切都好像有了新的标准,感觉被投入到了另一个超现实世界,又必须得去适应它。也会收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反馈,需要随机应变。结束录制后,我们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了两天放松了一下,回来就一直在看书,写一点东西,恢复一点生机。 大多数时间,每天还是处在创作焦虑中,必须得写点东西出来,才觉得这一天过得有价值。其实很多时候是写不出来的,就开始陷入自我责骂;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就继续写。这个过程中最吸引人的依旧是真正读到好的文字,以及自己写出一些好东西的时候,就会感受到活着的感觉,这种感觉会让我们追求一辈子。 我俩现在在分别写自己的小说、剧本,也时常在文学和脱口秀的语言中来回切换,但小说依旧是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只在一个领域里面完全发掘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然,写作离不开脱口秀演员的身份,或者说离不开这份工作,脱口秀能教我们很多喜剧技巧,但如果彻底脱离了小说,就没有让我们活下去的那种东西了。文学有真正可以改变现实的力量,是现实世界中破冰的力量,而且文字实在是太美了,无法抗拒它的美。就像拉斯·冯·提尔说的,“如果一个事情不极致,那为什么要去创作?” 明年,希望可以把舞台剧写好去演,脱口秀中专场的概念,如果能上映就好了。小说也写了四万字左右,感觉写不完了,太喜欢改了;会是一个短片集,关于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失望与尴尬,最终形成的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我们也发现,身边的一些朋友,有些并不是创作者,今年也开始有持续记录,好像人生进入这样一个魔幻的时代,应该写点什么,记住些什么。 回到我们,单纯就是很幸运,人生很多事情就是由运气组成的,成为颜怡颜悦就是我们最大的运气。我们之间,就如同一场早恋一样。(颜怡说,“颜悦是一个充满灵感的人,我经常不知道她的精力从何而来,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通道,我可以通过她走入另一个维度的世界。”而对颜悦而言,颜怡就如同《盗梦空间》中的那只陀螺,帮她锚定现实。)我们彼此是最聊得来的朋友,同时也是亲人,但我们选择以分居的方式共处。 其实,选择分开居住挺久了,一晃将近两年了。 每个女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哪怕是跟另一个人共享都不行。有自己的房间才有自己的大脑,相当于是在自己的脑内思考,而不用去受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决定哪怕多花点钱也要分开住。 但有趣的是,虽然是分开居住,但房间完全没有装扮出自己的个性,所有朋友来家里都嘲笑我们两家一模一样,有一些花花草草,有一些书,一些家具也是彼此帮忙选的,最终两个家就变得一模一样了,是某种自以为有主体性的愚蠢。 分开生活,能不能外放音乐成了一个最重大的改变。(有时候颜怡早上起不来,就会外放一些音乐或者博客,但如果是颜悦在旁边,会不好意思。而颜悦有时候播放音乐或是日剧,颜怡会在一旁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很吵,但现在少了这种声音,反而很不适应,就像是一些小小的节拍。)我们在音乐品位上其实很相似,只是谁放的音乐,就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导致互相绑架,谁起床就听古典乐啊。 我们两个住得不远,其实离得很近。回头看,分开住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是个正确的决定。当然,如果没有封控,就更好了。 直到今天,我们在微博上依旧共用一个ID,对于使用社交媒体在网络上发声,总隐隐感觉是一种过度的权利,越快捷的渠道越不会被严肃对待。社交媒体并不是我们的自我,恰恰应该对外展现自我的反面。 对于网络上负面的声音,其实挺难排解的,我们只能说尽力了。一个恶毒的评论,即使知道对方说的很傻,但带来的影响还是远远超过十条好的评论。有些事情真的很难去美化它,或者说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难过,脱口秀的表达可能很难不引起争议。 人真的很脆弱,反正有时候我们是挺脆弱的,但面对这些声音已经成为工作的一部分,判断他人的评价是否有意义。我们会选择去听一些自己信任的声音,身边信任的朋友、平台的反馈,根据这些去做出调整。但实际上,哪怕是最不信任的人,或一个陌生的网友,他们的话依旧会对我们造成影响。我们所讨论的话题,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有一个新的阵营。 所幸我们还足够幸运,能够用作品说话。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会用作品去表达,这会让我们心里更有安全感一些。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拆分微博,就会把对方的名字作为ID,挺闹心的,对吗? 撰文:李冰清 我一直记得十多年前在欧洲的一次经历。老式地铁没有电梯,我守着两个20多公斤的行李在楼梯下欲哭无泪。刚飞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虽然感觉已经半虚脱,但作为穷学生,也只能自己咬牙继续这段折腾的公共交通换乘之旅。 一下搬两个箱子显然是不现实的。当我颤颤巍巍把一个箱子扛上楼梯时,突然发现有个胖胖的姑娘干脆利落地把另一个给我提了上来。对她来说这显然不轻松,因为一口气没歇,她的脸涨得通红。我不知所措地百般感谢,她也只是朝我挥挥手,“一路好运啊!” 我记得自己当时还感慨了一下,那天的地铁站里来来往往那么多男生,或许帮我搭一把手不是难事,最后却是一个女生帮了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外国人。当然,他人的帮助本来就不是必须的、应该的,但也正因为这样,那个女生的帮助才格外珍贵。 又有一次在泰国旅行,我一个人坐火车从曼谷去往素可泰。即使不怎么认真看新闻,也知道当时时局有些不稳。绿皮火车的报站方式就凭广播,我完全不懂泰语,很怕一不小心就过了站,所以一听到广播声就小心翼翼张望个不停。一位坐在另一边窗户的老太太见我如此这般三四次后,主动问我去哪里,她流利的英语让我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我们便有一句没一句聊了起来。 她是曼谷出生长大的华人,和先生在曼谷开了个饭店,这次是去探望女儿。她知道我要去素可泰之外还打算去清迈,便嘱咐我路上小心饮食,怕我受不了北部餐饮的辣度,又给我看了几段新闻,让我一个人小心、再小心。她和我同一站下车,我需要再换长途巴士,她让来接她的家人把我送到车站,看我买好票上车才挥手,“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和朋友提到这个旅途中的插曲,她一边和我一起感慨老太太的心善,一边又埋怨我心太大,万一、如果遇到怀有歹意的陌生人,在异国他乡的后果无法设想。可能真的是幸运,但在当时,老太太那样诚恳的微笑,让我无法竖起任何戒备。她说,自己年轻时也喜欢一个人在各处旅行,知道一个女生在路上不容易,她所做的不过是举手之劳。 我在旅途上还遇到过许多次类似的帮助,不管年龄、国籍,她们都是女性。后来我想,在她们主动向我伸出手的瞬间,或许都有一些无意识地将心比心:她们可能遇到过类似的境况,也可能作为旁观者,能感同身受我的无助。她们没有目的,好些人我甚至没来得及好好感谢就已经潇洒离去,但却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和慰藉。 从这些萍水相逢的人那里得到主动、直接的帮助之外,我还从许多遥远的女性偶像那里得到过启迪。当然,我有一点小小的便利,因为工作就是做采访,所以在看到资料之外,也有机会和她们当面聊一聊。我只是一个信息的传播介质,但从我自己的感受也好,从读者的反馈来看也好,这些女性的经历、在关键时刻的决定虽然更多只关乎于她们自己,却能给予很多女性勇气。 看李娜的自传《独自上场》的时候,我很惊讶,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也会被各种批评和质疑包围,因为信心的起伏感到困扰。当我们仰望她的成绩时,她默默吞下了伤病、疲劳、诋毁等等苦涩。 后来终于有机会采访她,她有点神秘地问,你知道第一次拿到大满贯的兴奋感能保持多久?不到两个小时。面对全场的欢呼鞠躬、去后台准备新闻发布会,她差不多已经冷静下来了。她很快就要面对下一个赛场,又要面对一切不确定的因素:不知道是否适应场地,不知道自己的伤病是否会复发,不知道对手的状态。 我当时怔怔地说不出话,强大如李娜,原来可以这样剖开自己的脆弱。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不安感如影随形,相比男性,我们对于自我的不确定感要强烈得多。当我们看到一个不断刷新记录和创造奇迹的女性也与我们有类似的感受,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也不懦弱。即使我们不可能成为李娜,但在面对生活中一地鸡毛的挫折时,至少可以像她那样坚强,去直面自己的缺漏和问题的所在。 惠英红是另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采访对象。她在年过50之后,横扫华语电影各项重量级奖项的影后。少时她以乞讨为生,中间她退过圈、开过美容院,抑郁症最严重时自杀过、重新做回艺人时被人鄙视过,但即使是极小的角色、极普通的作品,她都能让人看到独属于她的光彩。 没有什么随手得来的机会。最初她只能在后排演配角,在女主闹脾气玩消失的时候,她可以用一个漂亮的下腰赢得导演的青睐。她一早得了香港金像奖影后,开美容院的时候,即使知道客人故意刁难,也照样蹲下去为他们换鞋。重新回去拍戏时,化妆师拖时间不愿意给她整理妆发,她一边哭一边想,我总有一天要把尊重赢回来。 她喜欢《血观音》的故事,见导演时就直接把自己打扮成棠夫人的模样。她说,你想要的机会就努力去争取。人生总有高也总有低,但即使一次次走入低谷甚至绝境,都可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前提是你没有放弃自己。 年龄是许多女性担心的问题。无可否认,到了一定年岁,女性可以拥有的机会并不那么多,无论是家庭的责任,还是生理机能的衰退,都会让她们觉得“大概也就这样了”。 但惠英红的故事让所有人看到,即使到了50岁,还是可以开启人生的新天地,还是可以让所有人认识到自己的真正意义。 “女性”或许应该被看成一个群体。她们更容易共情别人的感受,更愿意实实在在去帮助同为女性的他人,也更愿意分享自己经历,而在“给予”的同时,她们对所有的“得到”也更懂得表达感激。这种互相的激励和支撑,让我们可以面对自己的弱小,却并不会感到孤独。 撰文:胡南 摄影:Irving Penn,美国版VOGUE 1980年12月刊 真正让我们动容的,从来都是善意和相助本身,无关其他。 雨天从身后撑过来的一角伞沿、雪中从寒冷里燃起的一丝炭火、泥泞里向摔倒的你伸来的一双手,甚至在黑暗与恐惧中从遥远的屏幕那端传来的一声不要怕……人们在脆弱和无助的种种情境里,被这些善意和相助的力量感动、鼓舞,而后将这种也许微弱但从不渺小的善意积攒、散播开来,成为下一个情境里帮助和温暖别人的光亮的种子。 细想来,这种善意和助力本身就是开阔宏大并且简单纯粹的。它从来不因种族、人群、取向、观念、价值、地位的不同而划出细分的范围,甚至无所谓来自陌生还是熟悉,源于有意或是无意;也就更加无所谓因为一个口号用性别划分把它圈定在一个二元对立的小格局里,绑架同性,驱逐异性。 有些人不惜用生命抗争的,不是某个狭隘的政治观点,而是人性里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在女性漫长的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历史上,向来也不是只有女性在为女性战斗。 我们因此更应该了解:女性抗争的对立面,从来不是另一个性别,而是阻碍着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向前发展得更加公允和美好的那些深深的偏见和歧视,是没能让弱者也可以不必担忧地走在路上的那些缺位的法律法规和社会秩序,是拦住我们向未知的可能性迈出探索脚步的那些沉重的家族规训和道德绑架。 在一个个令人发指的女性被害事件中,那些挺身而出伸出援手的女性越是令人敬佩,这个世界也就越是令人感到分外的悲哀失望。因为,如果当一个女性身处险境,只敢向同性求助;当一群女性身处险境,只有同性相助,多么可悲。这理应不是,也永远不应该成为“girls help girls”的初衷和结果。一句口号虚无而空泛,我们应该了解并身体力行在每一件小而具体的事情里推崇的,是且原本理应就是“person help person”,是帮助本身,是秉持正义者帮助受害者,是有余力者帮助弱者,是能发声声量大者帮助无声的人,是一个正向不偏颇的社会公义和秩序帮助和保护所有人。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girls help girls”?因为理解,因为共情,因为感同身受,因为你也可能是我,我也可能是站在困境里的你。 波伏娃在《第二性》扉页上写下“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在这个毋庸争辩的男权社会里,女性是他者。每一个女性从出生到长大,难以避免地接受着这个男性主导社会给予的准则,告诉女性应该长成什么样子。首先应当是身份而不是自我:是乖巧孝顺的女儿,是贤惠包容的妻子,是慈爱牺牲的母亲;是能被人喜欢被人选择才不算失败才算有价值;被要求完美地循规蹈矩而鲜少被鼓励勇敢试错;听话顺从、温良恭俭被大肆赞扬而少有人教育我们怎么自信从容地表达不同,怎么友好坚定地处理冲突。 性别低位感带来的羞耻心、被低估的能力和价值、被否认的追求和需要、被理所应当要求的额外努力和贡献、被忽略的想法和情绪,这些也许确实不是那些没有同样经历过的男性可以真正理解和共鸣的。生理结构的差异、复杂的激素分泌状况、经期、生育带来的那些疼痛和变化,也许确实不是站在另一头的男性可以真正感同身受的。 同为女性,我们在相似的经历和感受中成长生活,又普遍更加敏感细致具有同理心,更能察觉到并懂得彼此的难处和需要,也整体上更倾向于表达和回馈情感,于是更容易在困境中向彼此伸出手。在这个层面上,“girls help girls”着实是一句出自同性别优势的温暖又有力量的宣告。 轰轰烈烈的“ME TOO”运动由一个个境遇相同的女性受害者掀起被欺侮被伤害的事实,由一个个女性站在她们背后声援支持,更有女性律师、女性心理医生站在她们身边疗愈帮助。摒除掉个例背后种种复杂难辨的原由纠葛,其更为深远的意义也许在于,这些将恶公布于众的声音让更多不知散在哪里未敢发声的受害者们明白自己并不孤立无援,明白被害不是自己的错,明白正义总还是值得相信和期待。如此这般声势浩大的同性相助或许终有难以抵达之处,也或许终不具有更广泛的普遍适用性。但每一件小事上的同性相助却从来逊色半分。 有个小女孩曾在网上发出一条求助帖子,她因为月经初潮生理期量大总会弄脏床单,妈妈总因此责备她太笨,对于她想用生理裤的请求也被认为是娇气。小女孩因此自卑又无助,更不知道可以开口向谁倾诉求助。帖子下面充满了女生的评论,有人科普生理知识,有人安慰她非常正常不必月经羞耻,有人直接快递了生理裤给她。连妈妈都粗暴以对的小女孩敏感脆弱的青春期心理,被一群陌生的同性细心地呵护着。小女孩的幸运,很大来自于她知道求助。然后,她才能知道这个世界上妈妈不是全能的,但还有很多善意会向她表达理解,会帮助她理解自己、理解女性。 某电台采访一个在大城市独自打拼的女生,其时已是个大型企业的中流砥柱。她说刚工作时的上司也是一个如她现在这般的女生。入职的第一天,上司发给她一份细心整理的《女性独居生活指南4.0》,说是前辈们传下来的总结,里面细致罗列着一个独居女性应该注意的方方面面,每一条都俨然是一个有着陌生又相似面孔的女生鲜明的过往。现在她把自己的轨迹又修订了进去,更新成了5.0版本。团队招新遇到独居的女生也总是按惯例一样地发给她们。在职场和生活里都如斗士一般坚强独立的女性,也从他人的关爱帮助里汲取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力量与智慧。 2023的倍耐力年历宣布将由女性摄影师Emma Summerton掌镜,她是第39位倍耐力年历摄影师,也是第5位为倍耐力年历掌镜的女性摄影师。她将第49 版倍耐力年历的主题定为“致缪斯的情书〞,以此献给她的缪斯们,那些在她的创作道路上指引、启迪、带给她源源不断灵感的精彩的女性。 我想,这似乎才更接近女性互助的根本要义:你是这样独特美好,因此激励帮助我成为一个独特美好的自己。一个个自由勇敢地追求独特美好的自己的我们,因此激励帮助女性作为一个整体,骄傲平等强大地站在人群里。 编辑:孙莉 Teresa S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