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行走,都是新的发现。不光是发现更美的风景,更是发现更好的自我。我们本期特别邀请了三位美好生活记录者——作家安东尼和张怡微,家居服品牌创始人凌立程,看看他们在行走中如何发掘点点的灵感火花。
摄影:Serge Balkin,美国版Glamour 1942年5月号 
撰文:安东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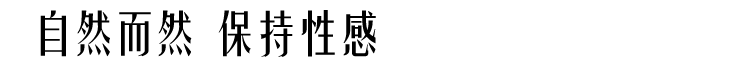
春天的时候 接到Le Labo的邀请去纽约 上一次去纽约差不多十年前 我记得带了很多的行李 心中各种期许 这次收拾行李 只是想着怎么少拿 因为只有三四天 装了登机行李就出发了 我的公关小茫和我说 你去美国记得多拍照片视频 发发小红书 和抖音 我嘴上说好 但心里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发 我是随着博客那个时期开始写作的 在那样的平台 有很多想发的 生活的点滴可以很自然的表露 没有什么遮掩 会写一些很无聊的东西 里面也有些真挚的感情 同样的东西放去新的平台 总觉得不适 小红书 太美 抖音太欢快 在上面总有不自在的感觉 好像博客时期 自己就是自己 但新的平台和媒体 大家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 发差不多内容 总有比你更会写的 更好看的 更有趣的 所以我就不再更新了 现在这些新媒体的很多内容一直都是公关在发 我自己不怎么弄 尽管知道这些新的平台很重要 但如果做不到与时俱进 知道如何割舍也很重要 墨尔本到LA这程 我飞的澳航 一直有澳航情结 因为他们广告做得好 经常 广告曲一出 听个前奏我都要哭 但他们的服务经常很差 没有亚洲航司那么周到 这次我飞澳航商务舱去纽约 飞机进入平流层 一个长得像老师一样 棕色皮肤的阿姨 走过来 她有点淘气地说 你两天后要怎么庆祝啊 我说啥?她说 你要怎么庆祝你的生日啊 我一听蒙了 心想 你怎么知道 我笑着说 会和朋友一起庆祝 她问我想要吃啥 我说我已经吃过晚饭了 准备直接睡了 你能帮我拿一杯香槟和拖鞋吗 澳航阿姨说 让我来想办法 商务舱现在只有睡衣没有拖鞋了 坐在11E 的女生说 我也要脱鞋 阿姨说 商务舱现在只有睡衣没有拖鞋了 他过生日 所以有特殊对待 11E有点失落地说 真幸运 没过一阵子 阿姨就拿来一杯香槟 和一双拖鞋 我道谢 喝了香槟就睡了 睡了三四个小时 看了两场电影 Zodiac 和 Close 还有一两个小时就要到了 这时候 阿姨又来 她蹲下来问我 飞得怎么样 生日男孩 我笑着说 很好 她说 你平时喝什么酒 红的 白的还是香槟 我说 我不喝了 她笑说 是给你的礼物 可以带走 我说啥 也太甜了 那香槟吧 她笑说 我猜就是 结果她再回来时候 带着两个澳航大叔 其中一个还带了兔子耳朵(可能因为那时候 复活节) 我心里想 千万不要唱歌 结果 两个大叔就开心地 唱起来 生日快乐 完全没有在害羞 他们一边唱 阿姨给了我卡片 和一瓶香槟 我说太谢谢你们了 估计脸红了 但我这次没带 check in 行李 就拿了个小行李箱 要把酒在机场 送人 还是不清楚他们怎么知道我生日的 太久没飞 我澳航就是普通会员 也许是 纽约的客户安排的?不清楚 爱澳航又多了点 到了LA 四小时后 转机去纽约 因为平白多了一瓶酒在包里 也没有机场免税店那种塑封包装 我得从机场出来 重新check in 才能过安检 LA机场很大 出机场后我就一直在想办法怎么解决这瓶香槟 来纽约之前 和在纽约做摄影师的朋友约见面 他说正好 他去LA之前能见到 那晚上 他什么都不安排 就来见我 结果飞的前一天我们视频 发现 乌龙了 我弄错了时间和日期 我到纽约的早上 他正好从另外一个纽约的机场飞LA 对此他特别难过 还说我很笨 又开玩笑说 中国人算术不是应该很好的吗 我一直抱歉 也很失望这次不能见面 拖着行李走在外面路上的时候 我在想 也许我可以把这瓶酒藏在 停车场旁边的花坛里 等他第二天到了LA 可以来拿 但一想 在机场附近偷偷摸摸藏东西 也许会被抓 而且 花坛 我要怎么定位和形容给朋友呢 说不定 反倒给他添了麻烦 又想说 要不要找个那种 输密码的储存柜 放进去 等他来拿 但那种柜子 取东西的时候 应该需要付款 我不想送礼物 还到付 然后就打消了这些念头 想说 要么就打包带去纽约 送给Kei 要么就送给一个路人 去柜台办理登机 一个美国黑人大妈帮我操作 她在系统里找不到我的机票 后来去机器上找到了 问我有没有 check in 的行李 我说 我就有一瓶酒 是从墨尔本飞过来的时候 因为我过生日机组人员送的 我说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这样我就只剩下随身行李了 她的脸一下子亮起来 说真的吗 这个月也是我的生日 还有三周 说着我把酒递给她 说 生日快乐 她快速地接过去 放到脚旁边 看着非常开心 她帮我添加了 新加坡航空的常旅客号 然后告诉我怎么走 笑着和我道别 然后我就又回到机场 休息室 层高很高 我坐在里面看外面的飞机 美国对我来说 并不亲切 一直有距离感 我和那谁视频 那谁说 我知道你下周回上海 这几天赶快把答应你的 遮光窗帘 安好了 这几天上海空气质量很差 我还买了两个 空气清新机 这时候机场忽然下起大雾 很直观地 看到大雾袭来 覆盖了一架架飞机 心想不知道等下 是否能顺利起飞 再登机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 那时候我已经很困了 放平了座椅 什么都没吃 就又睡过去 再起来的时候 发现飞了两个小时不到 有点不爽 本来目标是 睡一路 然后到了纽约就开始工作的 看了几集屏幕里 Sex and the city 觉得很累又躺下 美联航的飞机上 耳机里提供白噪音 我躺着 换了几个白噪音 还是睡不着 就那么硬挺着来到了纽约 刚出飞机 有冷气袭来 但真的到了外面 似乎也没那么冷 早上五点 天刚刚开始放亮 我和我的司机发消息 找到了他 上了面包车 往酒店走去 看着远处的桥和剪影 心想 我又来到纽约了 真的是个好大的城市 我和司机说 天气很好 他说前几天特别冷 然后有一天快要25摄氏度 感觉像夏天 接下来几天 天气都不错

酒店在中国城和小意大利旁边 走路可以去Soho区 是一个老银行改造的 名字叫 Nine Orchard 开门进房间 桌子上放了品牌送的礼盒和手写信 去洗手间 浴缸对面能看到 公园 港口和非常纽约感觉的建筑 早上的阳光流淌进房间 一切都是蜂蜜的颜色 我决定不休息了 往浴缸里加热水 挤了一些Santal 33 的沐浴露进去 于是整个房间 增添了柔软的老木头的质感 坐到偏热的浴缸里 呼吸着空气里的香气 看着窗外花园里 枝头上挂满鲜花的树 心里对 这次旅行有很好的预感 设定好闹钟 一个多小时以后 开始工作 进入纽约时间 再起来已经是 十点多了 大家十点半在楼下集合 看到一些很优秀的媒体人 我们坐车去 Nolita的店 我没睡多久 觉得身子还有点飘 进到这个店 我才意识到 之前来过 和Jess Harry 来纽约那次 我们住在Soho 就在旁边的街区 我们三个逛街来过这里 当时Jess 还买了瓶香水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瓶子不太起眼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又回到这里 太阳透过玻璃射到店里来 暖暖的 把毛衣脱下来 放到包里 中午在一个Dinner 吃了饭 我和 凌立程 还有 陶立夏 分了几个色拉吃 吃了很多东西 想赶快恢复体力 好好工作 下午又去了另外一个店里 这家店 香水和洗护是分开的 试用了一些产品 回到房间看到很多礼物 蜡烛 香水 洗护 我很喜欢 这次住的 Nine Orchard酒店 的这个房间 浴室特别明亮 能看到楼下不远处的花园 远处的水 还有桥 房间的音响 我太爱了 操作起来很怀旧 又简单 叫Ojas 搜了下官网 没有卖的

放洗澡水 挤了些 Santal 33 的沐浴露进去 顿时变成了泡泡浴 我躺进浴缸 闭上眼睛 被她檀香 的味道包围 我能明白 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这款香水 很成熟 但不装腔作势 厚重 但又不复杂 对于我来说 33不是适合我的香水 总觉得太温润了 像是一把坐久了的椅子 一张用久了的书桌 不想一直带在身上 感觉很适合用来做沐浴露 或者蜡烛 只要一闻到 整个人就放松了下来 即使在不熟悉的空间也有了安全感 好像是一个温柔的结界 像一个拥抱 我最喜欢的香水是 THÉ NOIR 29 和 Rose 31 这两瓶香水 后来我自己买了用 THÉ NOIR 不知道唤起了我哪一段记忆 每次闻的时候 明明已经呼吸到底了 总忍不住想要再用力呼吸下 感受更多 它游刃有余 但又不骄傲 让我觉得很舒适 经常睡觉之前用一些 对我来说 它是一种介于睡梦里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味道 我买了小瓶随身带着 想要自己感觉轻盈一点的时候 就用一些 Rose 31 光听名字就喜欢上了 我很爱玫瑰 但开了花店以后却很少进 做作品的时候也会尽量避开 觉得玫瑰太美了 放在任何作品里都是明星 久而久之就很无趣 但这瓶31 不会让人觉得无聊 它玫瑰的味道一直变化 不像很多香水品牌的玫瑰做得清新 甜美 31的玫瑰一直在变化 有鲜切玫瑰的轻盈和干净 一会儿又变成 尘土里努力扎根的 生命力旺盛的蔷薇 过了一阵子 又变成中东香料市场 麻袋里放置的干燥的大朵玫瑰花头 31喷在身上 不是在身上绽放花朵 而是在衣袖和皮肤之间存在 玫瑰夹在水泥里那种坚定和距离感 香水瓶子不精致 每款香水的名字也不梦幻 非常简单直接 白纸上印着给谁 来自哪里 在纽约的那几天 翻看酒店里关于 宅寂的书 上面写到:削减到本质 但不要剥离它的韵 保持干净纯洁但不要剥夺生命力 也许做到这一点 才能得到 真实 自我 和坦诚的勇气

生日这天 因为时差 起得很早四点就醒了 搜了下 附近Soho的 Barry五点钟就开门了 定了一节课 在前台买了运动短裤 男士更衣室里 陆陆续续进来健硕的人 偶尔有拿着西装袋进来的 想象他们可能 运动一下 六点多就去上班了 大都市人的面貌和举止都很不一样 锻炼完 天隐隐约约地亮起来 决定走回酒店

城市开始慢慢醒来 因为是四月 尽管清冷 但道路两旁 和公园里 的树 已经开着各种的花 吐着清新的绿 我大步向前走 有种莫名其妙的欢脱 就这样进入了四十岁 有些许变化 但好像 一切都没变
撰文/摄影:张怡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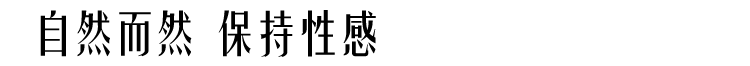
我的小说和散文中写城市,写上海的新村,并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因为,老社区在城市中的形态,越来越像散文,生发出一些别致的无用之物,这就有了审美的特征。“新村”是一个集体共用的词语,在马来西亚、在韩国、在日本,说的是不一样的社区群落。即使是在上海,鲁迅先生的故居大陆新邨、张爱玲女士的故居重华新邨,和我小时候生活的新村,并不是一回事。一个词,有不同的诠释,自带有不同的故事,这便很像文学的命运。多义、婉转、边缘模糊。

三年前,我搬到了现在所服务的大学附近。那是两个行政区的交界处。每个区都有每个区的园林审美,亦有每个区不一样的生活文化。很有意思。虹口区特别喜欢在街心花园里铺满黄色灯光,就连台阶边沿也要布置灯光。杨浦就是灰暗的,暗中有森严、亦有溢出森严的朴质。上周上班时,我路过邯郸路弄堂的转角,见到了奇异的场景。有个年轻男人,在路口用木板支起一个临时的摊位,上面放着一条黑猪腿。他和黑猪腿就并排站着。他的背后是由几家店铺拼接而成的,小门面的彩票行、机车行和麻辣烫餐厅。机车行里有一只看门的橘猫,我们都叫它机车咪。机车咪缓缓来到彩票行前,看了一眼黑猪腿。它好像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说的“我们”,包括当日四次路过摊位的我,以及来往的路人。那位青年很i,他不吆喝,也不介绍。他是猎人吗?他是在哪里打回来的野物。他运到这,又花费需要多久,猪肉不会变质吗。我仔细闻了闻,空气里没有腐坏的气味。那具不完整的动物的残肢,未经消毒检疫、未经现代化分割,就这样原始地、散漫地、安静地横陈在马路边。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出现在车水马龙的大柏树交流道边。这真让人好奇,也让人不安。 在它的对面,就是虹口区较大的市民菜场。在困难的岁月里,它曾也是附近居民想去而去不得的地方。有一段日子,菜场不便开门,就空关着。菜农在晚上,会把菜摊支到马路边,也就是那日黑猪摊位的周边。有生鲜肉类、有鱼虾海鲜、有蔬菜瓜果。还有消防栓上用记号笔写着大字:7点有肉来。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人抵制,像一种互相体谅。每个摊位,还会挂一个支付链接的牌子。但现金是流通的,因为现金不会记录行程。如今一切恢复正常,那喧闹的夜市,便成为了幻觉般的记忆,再也不复现。这些鲜活的记忆,是智能手机时代回光返照般的生活气息。我曾买过团购的猪肉、牛肉,却苦于家中连分割的刀都没有,对动物的肢体辨识,靠的也是互联网。那时我忽然觉得,我是被现代消费形态圈养的无能者。现代都市,看起来很亮丽,很有形式感。摩天大楼、精品橱窗。但这些“形式”,又都很脆弱。需要灯光、需要打扫、需要维护。然而生活本身,却可被精简去这些包装,呈现出实用的任务,和精神性的寄托。从对菜名的辨识,到时鲜程度的判别,再到手工的分割、加工,提取它的部分和其它东西进行调和。处理这些食材缓慢的过程,往往凝聚着长辈们等待孩子回家团聚的期盼,有时期盼会延长至一周,食材加工的时间也蔓延至一周,每天做一点,累计一点,发酵一点,浸润一点,最终才抵达团圆的结果。如果这个过程过速地完成,达到目的,那么便只剩下预制菜及其加热和投递。许多人不喜欢预制菜,是不喜欢添加剂和欺骗。但更多的人深表怀疑之处,恰在于它的形式是有缺陷的,不凝结真正的时间、炊火和个别性。它把我们对生活和饮食的形式的理解,给摧毁了。

不去屈从于它,会觉得更安心,更有古老的秩序感。有时我喜欢在附近的街区走走。例如沿纪念路穿过车站南路,能见到好看的复兴高级中学,这是一所老中学了,学校前身是“麦瑟尼克”学校,始建于1886 年,1915年迁入定名为 “汤姆 · 汉壁礼男童公学”。再往前走,会遇到一个驾驶员培训场。一直走到底,再也走不通时,就到了凉城。那是一个市民味道很重的热闹地方。夜夜有广场舞的人群,远远就能听到音乐声。广场舞落幕后,约十一点光景,会看到很多遛狗的年轻人,夜晚是他们的。这一路很寂寥,一点也不文艺,里脊肉7块钱买一送一,和文胸店一起开过深夜。有一次我在那里的电影院看张律的电影,我是整个电影院最后一个看电影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我提前退场时,电影院的售票员正在打游戏。他问我:“你还回来吗?我还没有打完”。我说,“太晚了我不回来了,你好早点下班。”有时我会在水电路转弯,穿过车站北路奎照路,就会抵达即将拆迁的万安路,亦是另一种风貌。沿路可能有四到五家红烧牛肉面的铺子,映照周围也许有不少喜欢吃面的人。也有不到一平米的小商铺,夜里还在卖买二送一的葱油饼,12块两篮的草莓,可见老江湾坐拥水网,买卖兴隆,至今依然看得到古朴的市声。许多矮平房都在拆除中,墙面上的窗户被水泥堵死。大大的拆字,让人梦回这座城市大兴土木的那些年。会有小孩攀爬到待拆建筑物的盯上,拉开裤子向下方尿尿。



有一些手机照片,记录了我city walk的冷门路线。如变电箱边的马桶,夜幕中粉红色的儿童机车,十分闪亮。小猫抬头看着树梢,它颈椎真好。树上则还有一只,它下不来,它上不去。被清空的垃圾桶边,有大只的废弃玩偶,可能是只大兔子。甚至在非机动车道上,会停有健身器材健身车,它看起来可以骑,其实又只能停留原地,仿佛生活的隐喻。一旦凝视这些废弃物失了神,很快就会被市声拉回现实。身后一个小哥哥对着我大喊,“开背送大鹅,要不要啊”,我前面一个推轮椅的阿嬷突然回头问我,“那你们38元几次?”我只能笑着快闪。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会让我忘却白天的苦恼,夜晚的焦躁。我好像一个没有主意的人,被静物吸引,被喧闹影响。在如今,于中年生活的遐思中,我重新发现了上海,发现了低科技、不方便的人与人之间。发现了可爱的精神价值,那是生活历练中才能萃取到的真材实料,是诱惑我一生的体裁。人为什么会想去陌生的地方走走。有时是因为一句话、有时是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 今年四月读书日那一周,我受澳门文化局之邀,去做了两场文学讲座。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去澳门的生活区走走,看看菜场、看看闲人、看看一日二十四小时,别人怎么度过。四月底天气渐热,时不时还有阴雨。但清晨是舒适的。我住在关闸东方明珠附近,靠近澳门最北面,酒店的落地窗足以眺望珠海。有一栋叫榕树的楼,看看就在那里,那么显著,其实是走不到的,因为它在海的对面。居民区附近有许多餐厅和公车站,清晨时分,就有人打羽毛球锻炼,虽然屋宇高且老旧,却很有生活气息。有几个傍晚,我还在居民区中找到了美发店洗头。我很喜欢在不同城市的居民区洗头,有很多表演的机会可以佯装漂泊的异乡人。记得有一次在广州办签书会,签售之前,我随便找了一间店吹头发,洗头的小姐用蹩脚的广东话对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你是不是就在这附近上班?”我说“对啊”。她说,“其实我不是广州人”。我说,“我也不是”。这种奇异的感受,仿佛是亲密的黯然,和对于信口风花的坦然。

行走最快乐的,莫过于“节外生枝”的部分。我在澳门读者的提醒之下,想去找一找的大圣园和哪吒庙。于是有一个白天,我从友谊桥大马路出发,沿着漫长的马场海边马路走到了罅些喇提督大马路,沿路经过了一座莲峰庙,邻旁是澳门林则徐纪念馆。莲峰庙初建于明朝,主要供奉天后娘娘,是澳门三大古庙之一,又名关阐庙、慈护宫,后因枕落莲峰山而得名。它建于1592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莲峰庙前空地是林则徐的全身石像,以纪念这位钦差大臣曾令澳葡当局禁烟的事迹。我会想进去看一看,出自隐微的缘由。几年前上海曾有一位文学院院长,早年曾负责缉毒工作,他很热情地与我聊天,突然说,“小张啊,明年是虎门销烟180周年,会在上海和平饭店举办活动,你记得关心一下。”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关心,又从何处开始关心。后来,我去广州做新书活动时,特地和朋友去到距离广州市区几小时的南沙看了一看,在虎门附近吃了一顿海鲜。南沙在广州的最南端,极少会有人因为巧合路过那里。天黑下来以后,在一棵树下,我们等车要返回宾馆,一等就是四十分钟。天气很热,学妹脱掉了高跟鞋,赤脚站在了地上。她也放下了手中拎着的新鲜龙眼。这种打烊感本来应该发生在更私人的空间里面,然而太累了似乎也顾不了那么多。我们好像还聊了一会儿女明星赵丽颖的电视剧,然后同伴突然很轻地说了一声,“其实前面的前面,就是伶仃洋”。于是我就朝着前面的前面望去,只望到一片漆黑。往前走了几步,也看不到虎门大桥。那时我又想起那位跟我搭话的文学院院长,我曾以极其拙劣的聊天技能,只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么请问院长现在上海哪里缉毒工作比较难做啊?”院长说,“你们浦东”。我如今也不住在浦东了。可如果不是那偶然的一句话,今年的我,也许不会有那样一段行程,不会走进莲峰庙,走进正在修缮的林则徐纪念馆,小转了一个小时。

出莲峰庙,会走过一整条殡仪馆街,分别属于镜湖医院慈善会、和天主教逾越园。一直走到白鸽巢公园附近的麻子街,停留了约四十分钟,不断问路,却好像没人认识“大圣园“。麻子街巷弄十分错综,往北有家冷巷、罣累巷,往东有红雀围、鸠里、海蛤里、珊瑚里。我在沙梨头斜巷盘旋很久,鬼打墙地询问,特别像小说中的迷宫之旅。我在居民区的一条小径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时还有沿街商户的工人在做焊接,他焊接完了准备收工时,我还没有找到路,浑身已经热得汗透。在平面无法找寻到的目标,我猜想在空间中也许会有可能,于是就找向上登攀的阶梯。最终在麻子街洞穴巷偏巷,终于看到了它。 行走,就是在凭借自己的方向寻找生活的形式。与工作有关、与情感有关、与一句话有关、与一个念头有关。有些场景,原先是隔膜的,走走就成了参与,就走过了远近的界限。有些人,原先是无话可说的,说着说着,就都成为了情景中人,成为记忆,和召唤。黑猪摊,也许一百年只会在这里偶然出现一次。伶仃洋,却一直在好友声音的尽头,是漆黑的存在。凉城并不凉,热火朝天中,并不那么热爱真正的艺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和“开背送大鹅”是一样的廉价,又一样的暧昧。它们汇聚在一起,储蓄着我的生命记忆,我记下它们的演变,也仿佛是在做一项十分基础的园林工作,修剪、拔出、焊接,再余下一些,再留有一些没有走通的迷宫,最终成为了文字的演变。那便是生活的轮廓。
撰文:凌立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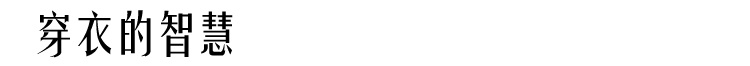
10月和11月在各个城市奔波,先去京都参加艺博会,然后去东京的艺术周拜访艺术家、见我的供应商,无缝衔接回上海参加西岸和ART021,还见缝插针去了一趟新加坡。 类似这样的日子要追溯到2020年之前了,那时候热衷于满世界参加艺博会,去美术馆、画廊的开幕。靠着两个行李箱,把艺术周过成了时装周。 有朋友对于我每次认真打扮出席各种场合表示出很佩服,当然是真心在表扬我。想来也许真的是因为职业关系,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在杂志做时装编辑,每个月都要拍摄”一衣三穿”的栏目,那时应该就注定了未来的我可以靠着两个行李箱和一衣多穿的技能,轻松游走在不同场合。 但这次在京都,还是出现了意外。 朋友Yukako是京都ACK艺博会的总监,刚参加完她的艺博会,Yukako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体验茶道,想到Yukako家族六代都在京都从事茶道,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猜想应该是一次小团队的体验活动,之后的几天我沉浸在京都美妙的寺庙和枯山水中,完全忘了追问细节。 直到我们约定日子的前一天,Yukako发来消息,”明天和Theaster Gates一起茶道,大德寺见!” 我才意识到原来是和我喜欢的艺术家,在我最喜欢的寺庙里体验茶道,那我应该穿什么?这次带的行李里可没有和服。根据以往参加活动的经验,如果dress down了往往会影响我的心情,而每次dress up了,身心不仅舒畅,也能更好的去享受过程本身。 问了身旁土生土长京都女朋友的意见,她笑着说自己好久没去参加茶道了,和服不一定要穿,但白色袜子肯定是要穿的,她这样建议我。于是赶紧查了京都的二手和服店,飞奔而去。 这家二手店位于京都市中心,一楼是二手衣,二楼整层都是二手和服,此时距离关门还有一个小时,很幸运收获了两件全真丝的二手和服,一件花朵暗纹香槟金色,内衬是极正的朱红,像极了Dries Van Noten会用的配色;另外一件是粉色的芍药图案搭配枯山水般的图纹,粉却不俗气。我还第一次试了女朋友提到的搭配和服用的白色Tabi棉布袜子,试过才知道原来日本女孩子都是纤纤秀足,不知道是袜子的版型偏小还是真的是我脚大,店里最大的24码试下来还是过小,于是果断放弃穿Tabi。 回到酒店搭配明天茶道要穿的look,决定依旧走混搭路线和永远舒适第一的原则,用我自己设计的Homeism的双色滚边真丝长袍、最基本款的真丝家居裤来搭配香槟金色的和服。考虑到身为游客的我明天茶道结束依旧会去探访寺庙,于是抓了件不易起皱的厚针织外套装到包里备用。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和Yukako约定见面的大德寺门口,她和Theaster Gates,翻译Michael已经在等我了,招着手朝他们走去。Yukako介绍我们互相认识,Theaster虽然戴着浅色玳瑁镜框但他的眼睛闪闪的,很热情和我打招呼,毫不吝啬夸赞我身上这件真丝长袍,说他很喜欢,并说有个小礼物要送我当见面礼,我笑着回应这件其实很像你平常也会穿的衣服。Theaster那天穿的是棉布工装改良套装,外面罩了件他自己设计的米色亚麻长衫。 天气非常好,我们聊着天走在石板路上,向芳春院走去。Theaster和我聊起他两年前在上海Prada荣宅的个展,他在杭州的旅行经历,我说我也很喜欢杭州,杭州的风景和文化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和京都很相像。

等我们走到芳春院,日本艺术家Yaman和茶道主理人Reijiro已经在门口迎接我们了,他们和Michael一样都穿了极其传统的和服。互相认识问好,脱完鞋我们准备进入寺庙,我拿起手上的和服穿在Homeism的长袍外,这个小举动引来了大家的关注和赞赏,让我有些害羞,我说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日本传统茶道,所以昨天去二手店买了这件30刀美金的和服,我有很认真在对待,虽然并不是传统的穿法。日本男孩子们很棒场说这件和服非常适合今天,Yukako坏笑着说我今天也应该穿和服来的。Theaster说你30刀能买到全真丝的和服,真的太棒了,it’s not about price!他随即拿出一双朋友为他专门定制的黑色皮质tabi袜子套上脚,原来他才是最有备而来的那一位!

我们边喝抹茶边听Yaman讲解他为芳春院做的在地艺术,中途我和Theaster这两个”老外”长跪到不行,一直偷偷换着腿的姿势想让自己舒服些,日本朋友们跪坐着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快中午时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封闭的小房间品尝Reijiro的怀石料理,Theaster即兴为我们高歌了一曲,几杯烧酒下肚,气氛越来越好,室内的温度也变得有些高。作为现场唯二的穿了两层的“外国人“我开口向日本男士们求助能不能开些门,他们欣然答应,随之流动的空气和门外的美景移步而来,京都的11月天气堪称完美。Theaster朝我眨眨眼睛表示感谢,他是真的被热到了。 午饭过后才是正式的茶道环节。去茶室前需要换上草编夹趾拖,再从小石路步入茶室。穿着正常长袜的我犹豫了几秒钟,脱下了我袜子,赤脚穿进拖鞋,第一个顺利进入了极其狭小的茶室入口。Theaster的皮tabi袜明显过于厚重宽大,他艰难得挤进夹趾拖,踉跄着进入茶室。日本友人们则神不知鬼不觉轻轻松松进了茶室,完全不像我和Theaster带着一丝狼狈。 品尝完浓郁的抹茶,这次茶道体验就正式结束了,我们一一告别,我换上了针织外套准备去隔壁的盆景园消磨这个下午。 人非常稀少的园子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修剪盆景,我晒着太阳,回想这两天在京都的遭遇,庆幸昨天当机立断去购置了和服,和Theaster因为打扮这件事有了共鸣,因为这件30美金不到的和服,带给我了一整天的好心情和难以用价值来衡量的美好经历。 穿衣的目的是什么?取悦自己,做舒服的自己,穿什么是自己的品味和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做自己的同时,得体、合宜适时比单纯的美或夺目更为难得,因为背后隐藏着的是观察、阅历和智慧。但质感和优雅是通往得体的一条捷径,这是我去了无数画廊开幕和晚宴后得出的结论。 行李箱和衣柜也并不是越大越好,旅行时反复在穿着的永远是那么几件羊绒或真丝的单品,这次日本旅行只带了一件外套,Burberry的经典卡姆登风衣,宽松的剪裁可以让我在东京白天日常的牛仔裤衬衫装扮和夜幕降临后换上晚装高跟鞋之间自由切换。 现在出门我还会多带一些简洁的首饰,以备不时之需,面膜和香氛蜡烛也是保持好气色、好状态的必备。当然旅行在外我也不全是个极简主义者,这次在新加坡只待一晚,我还是带足了四双鞋:球鞋、拖鞋和两双高跟鞋,万一呢?天知道艺术圈的人在想什么,与其这样,不如自己来创造惊喜。
编辑:张骞文Valerie Zhang
图片提供:Condé Nast Arch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