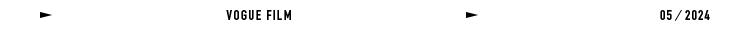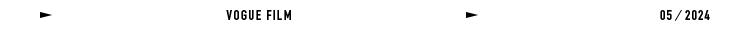
今年戛纳的短片竞赛单元,从4420部作品里最终选择了来自10个国家的11部作品。中国的入围作品《在水一方》来自导演李蔚然,她正巧是我们的“前同事”,在她多年的旅居生活里,也曾停留过那么一段时间,在VOGUE做一名视频编辑。而《在水一方》的故事雏形,便来自于李蔚然还在VOGUE工作期间的一次自驾之旅。那次的经历在她的脑子里停留了七八年,慢慢发酵成了一个被音乐触发、想从大山里走出去的女孩的故事。在24日的戛纳Cinéma de Demain晚宴上,李蔚然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第四届“Lights on Women’s Worth”的奖项,并从Elle Fanning手中接过奖杯,成为了当晚最被期待的女导演。
《在水一方》入围本届戛纳短片竞赛单元


李蔚然在戛纳从Elle Fanning手中接过第四届“Lights on Women’s Worth”的奖杯
有人跟李蔚然说电影长片是小说,短片是诗,小说必然好看,引人入胜,但是生活需要诗,诗可以引发一些想象和好奇。《在水一方》的故事很简单,但是余味很悠长。沙石漫天的偏远山区,路过的卡车司机在一个破旧的家庭面馆里吃了一碗面,煮面的女孩对司机的随身听产生了好奇,里面的磁带播着邓丽君的《在水一方》,轻言细语流淌进女孩粗砺的世界,让她有了走出去的渴望……
《在水一方》剧照
李蔚然现在生活在柏林,《在水一方》是她去年在敦煌拍摄的一部短片。与过往她偏纪实的作品相比,这次是一部虚构类作品。15分钟的片长,实际的拍摄周期只有五天,前前后后都算上,她在当地待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找钱花了一年,筹备拍摄又花了一年,剧本打磨则更久,差不多四年。如果算上最早的故事灵感发生的时间,可能长达七八年。“我感觉这几年我不停地往上面加上一层层东西,有很多可挖掘的我都试着埋在里面,但我也想尽量让它不那么累赘的同时,给到大家去探讨的东西,可以由每个人自己去填充这个故事。”李蔚然不想“解释”作品,不想“塞”给观众她的想法,她埋了很多“彩蛋”,看到多少,或者看没看到都是属于大家各自不同的观影体验。
导演李蔚然(Viv Li)
作品的年代设定并不明确——虽然看到袖套、老式暖壶、随声听这些东西,我们会下意识地觉得是八九十年代,但考虑到这是一个偏远的地方,也可能没有那么久远。想从山里去到城市的女孩是许许多多人的缩影,我们总是无法安于自己来自的地方,向往着另一头的世界。“当你在河岸的这一边,你总是觉得河岸的另一边更高,但是当你历尽艰辛游到那头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的河岸又变得比这边高。”李蔚然的作品总在探讨“抽离感”,这与她的个人经历关联很深。无论是在英国上学,在南美教书、做粗活,在VOGUE工作,还是现在在柏林做电影,她一直想要不停地把自己融入到一个群体之中,“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性,总有一种想成为团体中一员的感觉。”时间长了她有一点迷失,她把自己丢进到一个又一个地方,又从那些地方一次次出来。但执着于自己到底是什么可能也不太重要,电影给了她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但不是目的”,她补充道)。每次从写剧本到实际拍摄都会间隔很长时间,会让她在拍的时候觉得这是另一个人写的东西,可以跳出来回看或者审视自己。“所以任何形式的创作者都可能是会更加了解自己的人,因为他们在不停回看自己的创作,回看曾经的自己。”在这样“分化”出另一个自我视角之后,李蔚然总是可以在创作的过程里接受着各种变化,各种来自外界的信息、灵感,来让自己更好地传递创作意图和愿景。
《在水一方》的拍摄幕后(胶片日期没有调请忽略)

这次去到戛纳,李蔚然见到了对自己创作有着很深影响的评委主席格蕾塔·葛韦格,开幕式的时候,梅丽尔·斯特里普就坐在她身后那排,一切都是梦想成真的样子。但短暂的盛会过后,她继续回到细碎繁杂的创作与拍摄中。现在李蔚然即将完成自己的纪录片长片,内容是关于她在柏林的一些文化生活;还有一部刚起步的剧情长片。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她的影像路将继续延伸,无论逆流而上,或是顺流而下。
餐巾廓形西装外套Evening 耳环Unsaid 以下是VOGUE与李蔚然的对话
当你得知自己的作品入围戛纳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当时的心情如何? 我当时在马路上走,想去做个美容,因为觉得自己有点老了(笑)。然后突然有个法国的号码给我打电话,我还以为是我的销售之类,接通之后对方说他是Bruno Munoz,戛纳的短片负责人(Head of Short Films),问我在哪儿,我说在马路中间,他说你先移到边上去,然后就说恭喜你,你的电影进了短片竞赛单元,我们很喜欢你的作品。我整个人挺惊讶的,因为在出结果之前应该还有个类似于入围的“短名单”,制片人也没跟我说进没进,然后就到了四月下旬,当天还有三四个小时就公布入围名单了,我觉得自己肯定没戏,本来进戛纳也是非常难的事。结果好消息就来了。后来我做美容,给我按摩脸的人一直跟我说,小姐你不要再笑了,再笑的话我没法给你按了。
《在水一方》的拍摄幕后
这个消息你当下分享给了哪些人? 我肯定想分享给我国内的制片人,我说我有急事,想给她打视频电话,她当时在喝酒,还觉得我故弄玄虚,接了电话之后就特别激动。我也给我妈打了电话,她知道戛纳,但不太理解入围这件事儿,我就说,今年入围戛纳的有贾樟柯、陈可辛、管虎,还有我!(笑)她就明白了。因为我爸妈、我姥爷都是搞化学的,我也不是学电影出身,所以能进戛纳真挺激动的。 餐巾廓形西装外套 Evening 李蔚然与制片人叶先开(Sol Ye)耳环均来自Unsaid 我在英国上大学的时候,第一年读的是英语和语言学,当时选修了一些课,里面有戏剧,然后我就变得特别喜欢戏剧,就转了戏剧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太不好找工作了,尤其毕业之后,当时也不知道该干嘛,就去了南美做志愿者,待了差不多两年时间。那个时候我开始用摄像机拍一些东西,才有了‘我可以拍一些东西’的感觉。后来去了VOGUE,视频组会拍很多明星、时尚相关的短片,是跟我之前接触的不太一样的另一种创作视角。之后差不多从18、19年这样,我开始真正做自己的片子。
《在水一方》的拍摄幕后
跟你自己偏纪录性质、更日常和质朴的创作相比,VOGUE呈现的风格是更加都市的,有时非常华丽,这段工作经历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 之前我其实不太明白“fashion”的意义,我喜欢新奇或者搞笑一些的东西,但在VOGUE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所有的事情就是一个词,taste,品位,服装是一种品位,电影也是一种品位,怎么拍、怎么选择,镜头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故事为什么要这么讲,都是品位。这是一种修养,要长期不停地看很多电影,才能够去理解,并做出自己品味的选择。我想VOGUE的工作让我体会到了对品位的尊重。而且很巧,《在水一方》故事的缘起,其实就是发生在我还在VOGUE工作时候的一段经历。 我记得应该是15或者16年,春节期间我们有八天假期(VOGUE的春节假期通常比法定节假日多一天),我有个拍纪实的摄影师朋友,他说甘肃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基地,开几十公里都是风车,加上那里光照很充足,会有很多太阳能板,就很想去那里拍照。所以春节的时候我开车带他,高速路还免费,就一路开到了甘肃。沿途的风景都特别美,我也是第一次去,完全被震撼到了,有黄土,有山岩,又有雪。我朋友带了一个ALPA STC型号的相机,瑞士的一种外型很独特的相机,有点像机器人,有天晚上我们开了很久的车、特别饿,就去了路边一个特别小的面馆,进去之后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她先是看见一个外国人,又看到他手里那个特别唬人的像机器人一样的相机,就一直问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我对那个女孩的印象特别深,我们临走的时候,她一直看着我们,像是今天见了两个外星人。她的眼神给了我挺大震撼,我一直记得。我也会想,她是不是也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想着那个相机和我们。
《在水一方》的拍摄幕后
是一种被打开了新世界、开启新次元的感觉? 对。就像我们小时候第一次听周杰伦,会觉得还能这么唱?!后来我们又去了一次包头,有天一个保安抽烟的时候过来跟我们聊天,他说他年轻时候在工厂工作,有天中午吃盒饭的时候,突然听到旁边同事在听一首歌,那种老式的耳机如果声音开的很大,周围是能听到的,他说他当时饭都没吃下去,就去问这是啥歌,怎么跟之前听过的都不一样,对方就说是叫披头士。这个故事我也一直记着,我就觉得音乐的魔力真的很大,工人中午吃饭的时间那么宝贵,但是他能为一首歌停下来。所以我在《在水一方》里把相机改成了随身听,之所以选择邓丽君的《在水一方》也是因为我觉得不管在哪儿,菲律宾、日本、越南,你只要张嘴唱邓丽君的歌,总会有人能跟你一起唱,这就是一种穿越语言和国界的魔力。 影片的男女演员都是很生的面孔,是怎么选择的? 我先定的女孩,再去找跟她搭的男孩子。女孩我找了很长时间,见过很多演员,但感觉都不太对,因为现在每个人都特别的都市化,那种非城市的淳朴、天真很难找到。我记得当时每天都在刷小红书,突然刷到一个广西壮族的女孩,叫“痣多多小赵”,就让制片人联系了她,她发了一个试戏的片段,在那个片段里她自己琢磨出了一个西北的口音,有点霸气,又可爱又有灵性,我感觉她挺有天赋的,所以虽然她从来没演过戏,我们还是想赌一把,就定了她。第一天拍戏,拍的是女孩和男孩的对话,她特别紧张,但是到了第三天她就特别自然,学得非常快,情绪、微表情都有了。我觉得她未来也很值得期待。
《在水一方》剧照
影片中间有一部很令人在意,女孩听着男孩随身听里的《在水一方》,也没人说话,外面飞沙走石,房间里的两个人像是在另一个宇宙维度里,但是突然绞带,音乐被打断,那种断裂感特别强烈。 我其实是抵触强加给我的浪漫,有人拍电影觉得整个氛围没出来就加点音乐烘托一下,我会有点抵触。《在水一方》特别柔美,你听着听着好像会为小女孩感到同情,她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音乐,所以我中间插了噪音,就是屋外的环境,我想说我们听歌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听一首歌、看一部电影,就像在做一个奇妙的梦,我想打破这个梦境,我想告诉观众,你们进入到一个梦境了。 影片的结尾也不是特别确定性的,给我们留了一些空间。 *该回答涉及影片结尾剧透 我身边也有朋友说出了一些非常惊人的剧情猜测,大家都有自己的想象。我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女孩在自己的房间里,最后一个镜头是男孩在他的房间里,其实像是一个轮回,这个男孩曾经就是这个女孩,大家都是从乡下来的,到了城市以为可以有更大的生活,但日子也一样辛苦。所以这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当他们相遇、听磁带的时候,他们好像突然交换了生活。 《在水一方》的拍摄幕后 影片的道具、服装都非常有长年使用的那种老旧的质感,这部分是怎么筹备的? 东西是我们去老人家里借的,的确就是他们那么多年用过来的东西,衣服我们也去收了一部分,我们的服装还给我做了一个长长的pdf,一下让我想到在VOGUE的时候做的那种mood board。我想表达这个女孩是这个地方的一股生气,所以选衣服的时候无论是男孩还是老头的服装都很暗淡,但是这个女孩穿了一件黄色的外套,这件衣服虽然也是来自这里的、是旧的,但又很鲜艳。 影片的画面也非常美,每一帧都像油画一样。 去年柏林和北影节入围的片子有一部叫《小世界》,巴斯·德沃斯导演的,那部片子里的女演员龚丽悠是我朋友,也在给我的长片做剪辑,她帮我介绍了那部电影的DP(摄影指导),后来发现他是我师哥,我们在欧洲上过同一个学校。我就问他想不想来中国拍个片子,但是因为特别远,我们做短片也没什么钱,他就问他来能有什么好处,我说有非常多好吃的。后来他的确吃“疯”了,甘肃的大盘鸡、特别嫩的高山羊什么的。而且甘肃的山太震撼了,他虽然是被吃的“勾引”来的,但是他回去之后总是跟我说很想念甘肃的山景,我不用跟他说什么,山就可以告诉他很多东西。我个人非常喜欢黄棕系的东西,所以甘肃的整个色调都非常对我的口味。那时候我们每天早上4:30起,一直拍到晚上8点,每天从日出到日落的风景都是大家一起看的,还会一起在山上唱歌。这次去戛纳,我们也打算大家一起在海边唱《在水一方》。
《在水一方》剧照

这次是你第一次去戛纳吗? 我2022年第一次去戛纳电影节,我之前会觉得为什么去卢米埃看电影一定要穿礼服,要排那么久的队,要在看完电影之后鼓那么长时间的掌,但当时为了看汤唯的《分手的决心》的首映,我实际经历了这些,我当时心里就有一股热血在滚,我觉得这是多么尊重电影、多么庄严的仪式,尤其当我自己从头到尾去完成了一部电影,我知道这里面有多少苦,多少人的付出。所以我自那之后觉得一定要穿得很正式,去好好地欣赏电影。我也去过一些其他的电影节,但戛纳的感觉还是太不一样了。我自己就住在柏林,但柏林国际电影节就感觉还是属于这个城市的,但戛纳就完全属于电影。 这次除了入围,还有让我特别激动的一点是格蕾塔·葛韦格来当评委主席。我之前那部半纪录半虚构的短片《我在家中渐渐消失》就特别受格蕾塔·葛韦格早期一些作品的影响。我觉得选格蕾塔当主席是一个特别壮志雄心的事情。首先她是个女导演,然后她是从独立圈走出来的一个女导演,又可以导商业片,还那么成功,真的是挺震撼的。 对于拿奖这件事你怎么看? 拿不拿的都无所谓,进了戛纳就已经特别好了。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之前我一直在拍纪录片,也没有大的团队,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写剧本、跟几个朋友一起弄,其实我也有些虚构类作品,但是没有人关注到我这部分的创作。现在入围了,有了这样一个背书,我就可以继续去做我想做的事了,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编辑:Hezi 设计:小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