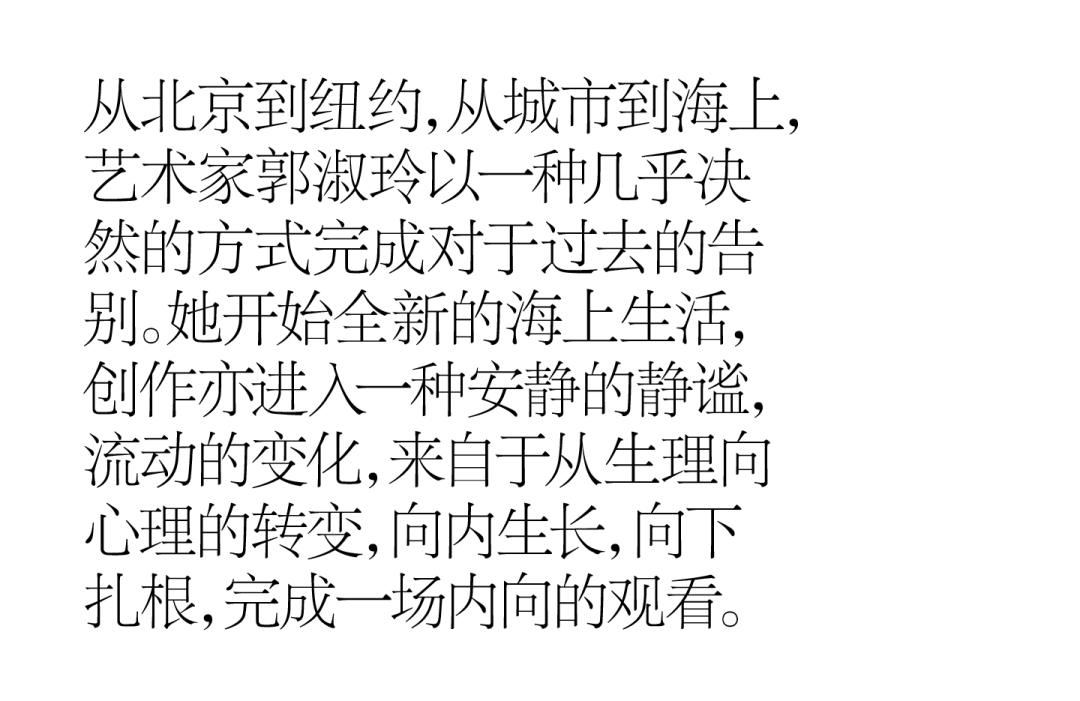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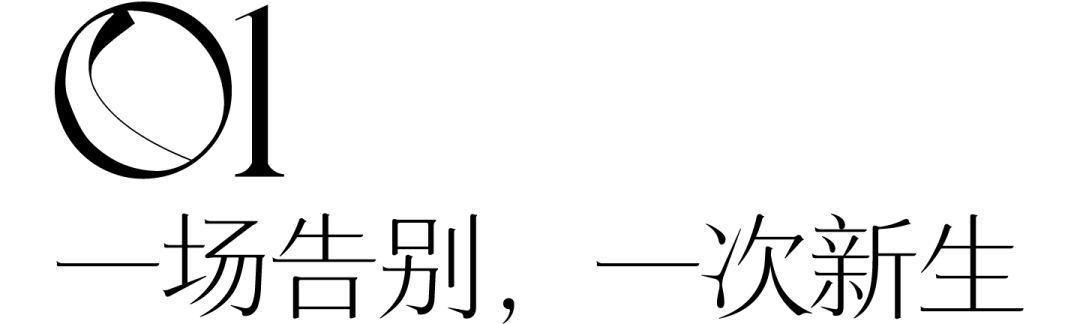
大学时期,郭淑玲就是一个叛逆的人。毕业于广东美术学院附中的她,放弃了广美的保送名额,毅然前往北京,凭借自己的实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的她同样选择“北漂”,经历了数年的北方生活。2019年,郭淑玲以艺术家的身份,前往纽约。
“我如果想要一个东西,就不会做第二个选择了,没有退路。”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做艺术家这件事,也没有退路。
在纽约的生活,让她决定换一种环境生活与创作,同时,和过往的生活完成告别。“远离了过去的生活,其实是和过去的所有的一切告别,和我在北京建立的所有关系,不管是生活还是艺术,告别过去的一切。这让我可以重新发展出一个新的自我。而现在的生活方式中,也较为离群索居。所以作品和我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
“我不是属于那种去建构某种哲学理论的艺术家,我的创作是跟随着我的生活而循序渐进的,感性的表达占主体。”
现在,郭淑玲坚持着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帆船上的生活方式。

郭淑玲还记得,自己当初最初尝试航海的体验。
“这种生活,很不可思议。美好,只是看上去很美。大多数时间,是充满挑战的。”
航海,大部分时间,是要仰赖自然的。旅途的进程完全取决于天气和风速,与岸上计划精准的生活相去甚远。当代帆船所配的燃油动力仅仅是靠岸与离岸时的辅助,超过90%的大部分的航程都会在关闭发动机的安静涛声中行进。驾驶者需要专心致志地关注随时变动的风力,灵活操纵舵与船帆来配合。

2020年,郭淑玲和先生一起,从加勒比的马提尼克出发,途经加勒比和巴哈马,前往美国北边,航程的距离有点类似于海南到北京,这趟旅行的目的是换一艘新的帆船。
“那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帆船旅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面对外海上的海浪,很颠簸,甚至有点晕船。甚至,当时我都觉得,可能要和作为航海爱好者的他分手了。”
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海上的景观和国与国之间地理的变化无疑打动了郭淑玲,她开始体会到航海这件事的美妙之处。
某日,当他们即将进入美属维京群岛港口时,有一大群黑白相间的海豚,围绕着、簇拥着,就仿佛引领她进入港口一样。有时在过夜的航行中,会有很多飞鱼就飞到船头的网上。“第二天,我就把它们白煮了,还挺鲜美的。”

帆船的船舱,其中一隅小天地,就是她的工作室。在她的创作中,大部分的中小尺幅绘画都是在船上完成的。而部分大幅的作品,是在她回到城市生活时,在位于费城的画室里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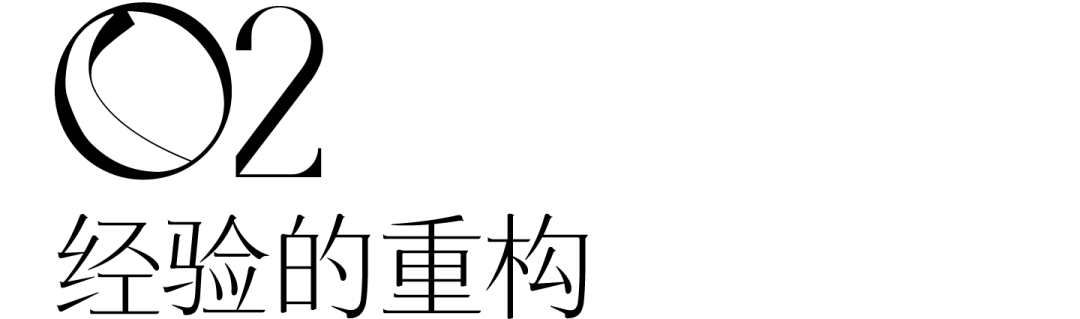
要放弃过去的绘画经验,绝非易事,是某种心理与身体惯性的对抗。
在离开校园数年后,郭淑玲的很多创作,依旧和写实挂钩,那时的绘画,也会描述自然,树木与花卉,其中间杂着光的流动,为她在帆船上对于海洋与自然的观看埋下伏笔。
郭淑玲在一遍遍去MOMA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她以前比较少关注的艺术家,用身体面对作品,如以巨大色块充满画布的Mark Rothko、勾勒流动性诗意形体的Helen Frankenthaler、长期居于荒漠中创作的Agnes Martin、全心沉浸于神秘学的Hilma af Klint等等。这种观看为她的转向,提供了某种共鸣,她开始进入一种向内发掘,与对于自我的探索。
这种创作情感上的共鸣,与郭淑玲在航海生活中的视觉经验,完成了某种交汇。美国东部沿海,那种面对大海的空旷,傍晚色彩的变化与流动感,浸入了她的创作。“不破不立,我渴望打破惯性,有勇气去面对有变化的生活,而不是每天在一个地方呆着,进入循环往复的工作。我想要打破自己,打破过往的成绩,以及所有为自己设下的圈套。”
郭淑玲开始在船舱进行创作,从体感到意识,都进入某种流淌中的自如。当然,船舱上的创作,有很多的难处,郭淑玲需要调整创作的状态去适应这种生活,比如只有在白天的某个时段绘画、面对尺幅的控制,与观看距离等问题,但在局限中亦可以寻找无限。





2020年,郭淑玲首个纽约个展“5—6 pm”,就记录了取自时间点的色彩,傍晚时分柔和渐变的色彩与过往那种激烈、对比强烈的色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个展“5-6pm”现场
如果说,“5—6 pm”是关于时间,那么最新的展览“低语”则关于空间。在新展中,郭淑玲以默读的方式完成绘画的创作,并为其标注坐标系,那些如珍珠般散落的小岛,不再仅仅是她航海生活中途经的过客,以更为隽永的方式,进入她的绘画之中。整个系列的名称中包括了美国东部的一些沿海城市以及加勒比海上的数个岛国,可以在世界地图上拼凑出这近两年间郭淑玲航海远行的大致足迹。系列名Sotto Voce则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她所描绘的亦真亦幻景象的境界和气氛。这个词来自意大利语,本意是以有意降低声调的方式表达重点。它也是乐器演奏的音乐术语,指示在演奏中戏剧性地降低音量,比一般意义的弱音演奏(pianissimo)更具有歌唱性和低声倾诉般的感觉,在莫扎特安魂曲和肖邦夜曲的曲谱中都能够找到使用范例。


个展“Sotto VOCE”现场
“航海的生活使人完全地裸露在自然中:风的声音,云的运动,浪的起伏,空气的干湿,鸟与虫的鸣叫,鱼和兽的搏动,这些事物重新塑造了人的性格。与自然不再是二元的关系,完全地进入其中,不分你我,与它一起生存。自我在自然的养育中像sotto voce一样,慢慢地低下来,直到隐没,这是人和自然最舒服的关系。”
海洋中的静谧,和城市之中的所谓片刻安静不同,某种时刻,这种静谧导向一种更为灵感敏锐的感知力。当被那种安静所包围时,整个人会苏醒过来。“回头看,过往的绘画显得有些繁复,我觉得和那时候所居住的城市气质也相关。当面对天空与海平面,没有任何的切割线,只有地平线,而海上其他的线条都是柔软的。在城市之中,很多线条都是直的,一整块天空也会被切割成各种形状,很难看清天空的全貌。”
她开始抛弃以图片作为记忆的物理性辅助形式,依靠图像的记忆和手稿,“照片是粗暴地截取某个瞬间,而回忆却具有感受的连贯性,当有一个想法要实现在画面上时,在一层层的上色过程中,大脑会经历对于图像的一次次推演。现在我开始领会,在画一个东西时,看到它,必须把它忘记,然后再去画它。不要直接画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而是要经历图像在感知中停留发酵的过程。感觉的真实比眼见的真实更鲜活可靠。”同时,整个绘画实践专注,依靠感知和意识层面上的真实,实现精确的表达。
“我居住的费城有一个巴恩斯美术馆,有非常多塞尚的作品,我经常会伫立在他的‘圣维克多山’前,想他那句‘风景在我体内思考,我是它的意识,只有深度专注才能约束飘忽不定的双眼’ ”。
在航海的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港口的停泊。“有时,我也要抵抗无聊,也在降低社交。每天会固定在甲板上做瑜伽。当进入冥想阶段时,航海中所看到的地平线,其实就非常接近冥想时的绝对安静,是一种左右对称的平行状态,这样的构图也经常出现在这两年的画里面。”郭淑玲说,“这也是我大脑中视觉化的意象。”
这种安静,同样如潮水,完成了从生活到作品的弥漫,海天一色,带有某种遁世的情结和灵性的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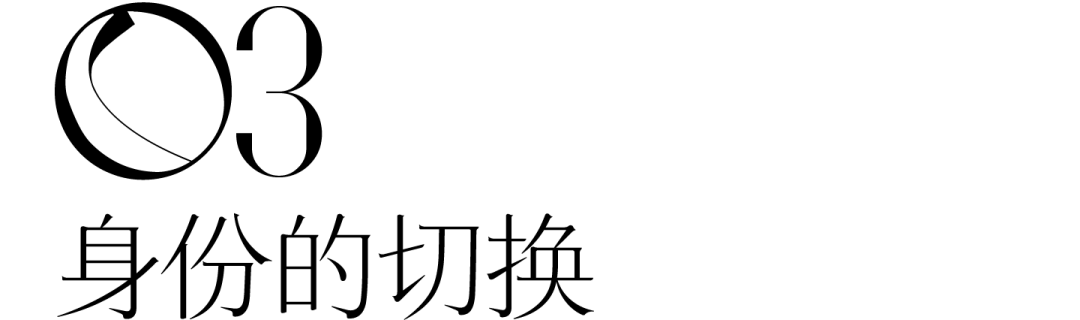
现在的郭淑玲,是一个“任职”时长刚刚三个月的新手妈妈。尽管有些意外和突然,但她依旧在适应着这种身份上的切换,与生活节奏上的调整,以及身体上的疼痛与疲劳。“现在的我,就暂时失去了在阳光下瑜伽的时间。晚上8点,孩子睡觉后,才会是我专心工作的阶段。”
有时,她也会带着宝宝回到船舱,在原本她工作绘画的区域晒太阳,画素描。明年年初,她计划和先生一起,带着宝宝,开始一场新的航途,跟随着自然的节奏,去追逐生活。“明年,会前往纽约长岛末端的一个港口,我先生的船曾经在那里停过五年。到时会途经纽约,会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再去目的地港口过夏天,待五个月,等到天气转冷,再继续往南航行。”

“现在我会逐步关闭一些频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停止吸取信息,我希望未来的创作,可以跟随着我的生活经验,与自然密切咬合在一起,向内生长,向下扎根,慢慢地接近我的精神内核。”
有一件事,是郭淑玲在航海中学到的,“大自然有它很强大的一面,不能去对抗,别去计划,保持观察。”她坦言,自己也经历过拧巴较真的过程,“放下执念,我希望创作走向一个平和、修复的状态,让自己这根连接自然与绘画的管道保持通畅和灵敏。”










